唤出我们的名
试看仅仅单个⾳节如何——
譬如杰克——能够舒展并化作
世界,圆满⽽完整,
当它是⼀个孩童的名
⽽于母亲唇间成形。
我曾在商场机场,餐馆⽕车,
⽆意间听到⼥⼈们
在交谈时撒落新⽣婴孩
或成年⼦⼥的名字,⽐如摩根或诺拉,
迈克尔或凯尔,约瑟夫或艾娃-罗斯,
每个元⾳和辅⾳都吟唱得
清脆分明,共振
如纯澈的钟声,⽆论奏响的
是骄傲强健的⼤调,
还是低徊的柔板⼩⾳。
有时,当我⼥⼉捕捉到
她⾃⼰的名字,伊莱恩·梅,
从我正电话⾥给姐妹讲的故事中掠过
之后她会半嗔半恼地问,
你刚才是在说我吗?
是啊,我⽆⽌境地,毫不羞怯地,讲述着
关于你的故事。我念着那些流动的⾳节,
为寓意——光明——⽽选
为韵律,为纪念你的祖母们,
在舍弃⽆数名字之后选定。
是啊,我⼀遍又⼀遍地吟咏它们,
并惊异于它们已成世界。莫⾮
上帝也如此唤我们的名?是否因此有时
当我听见风拂过树叶簌簌作响,
总会转⾝侧⽿聆听?
Saying Our Names
say Jack—can expand and become
the world, round and whole,
when it is a child’s name
being formed by a mother’s mouth.
I’ve overheard women in stores and airports,
restaurants and trains, sprinkling their talk
with the name of a brand new baby or
a grown child, say Morgen or Nora,
Michael or Kyle, Joseph or Ava-Rose,
singing each vowel and consonant
so they stand out, resonate
a pure bell whether the tone struck
be proud and strong, a major key,
or a diminished minor note.
Sometimes, when my daughter catches
her own name, Elaine May, part of a story
I am telling a sister over the phone,
later she’ll ask, quasi-annoyed,
were you talking about me?
Yes, endlessly, shamelessly, I tell stories
about you. I say those fluid syllables,
chosen for the meaning—light—
the music, and to honor your grandmothers,
chosen after discarding countless names.
Yes, I say them again and again and wonder
at the world they have become. Is this
how God says our names? Is this why sometimes
when I hear the wind rustling through the trees,
I turn and listen?
不知从何时开始,每当遇到的喜欢的字或⾳,我就会把它悄悄藏进记忆的抽屉,为了做母亲后,从中细细拣选,以呼唤我的孩⼦。起名,对我来说,是⼀个游戏,⼀次诞⽣,⼀种⽆上的创造。
每⼀个母亲都是造物主。当她俯⾝轻唤乳名,⼀个⾳节便挣脱虚⽆的束缚——如第⼀诗节中,单⾳节“Jack”在唇齿间舒展,凝成露珠,汇成星河,最终竟能扩展为圆满⽆缺的宇宙。玛丽安·墨菲·扎扎纳的《唤出我们的名》揭开了这隐藏于⽇常的神迹:命名,原是凡⼈最接近上帝的时刻。
《创世记》中,上帝以⾔语劈开混沌:“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母亲们站在商店货架前或⽕车站台上,将“摩根”“诺拉”“迈克尔”这些名字如种⼦般撒⼊谈话的⼟壤,何尝不是在履⾏同样的创造?
母亲呼唤孩⼦乳名的⽇常瞬间,就是⼀场模仿神性创造的庄严仪式。正如信徒反复诵念神名获得⼒量,母亲们也通过呼唤名字确认⽣命的存在。诗⼈锐利地捕捉到元⾳辅⾳碰撞时迸发的光芒——每个被吟唱的名字都在共振,清越如纯铜钟声,惊动了空⽓⾥漂浮的灵魂。
诗⼈恢复了取名的神圣性,但更重要的是,又将其归还⾄普通⽣活,并让被命名者对呼唤进⾏回应。母亲选择名字时斟酌”光明”的寓意,调配⾳律的节奏,编织祖母留下的丝线,在⽆数弃名的废墟上建⽴起独属于孩⼦的城邦。
⽽当⼥⼉偶然听到母亲在电话中提到⾃⼰的名字,假装⽣⽓地问“是不是在说我?”时,这个过程就完整了:呼唤需要应答,恰似上帝在伊甸园中呼唤“亚当,你在哪⾥?”(创3:9),等待⼈类回应“我在这⾥”。
诗中的声⾳不再⽆形,⽽是具备了⼀种雕塑感。扎扎纳让读者“看见”声⾳的形状:名字不再是抽象的符号,⽽是可被“撒落”的晶莹珍珠,有着钟声的圆弧轮廓与树叶的脉络纹理。这种通感令⼈忆起李⽩“⽟阶⽣⽩露,夜久侵罗袜”的凝露成珠——都是将瞬息凝固为永恒的艺术。
⽽当诗⼈听见风拂过树林簌簌作响,她突然转⾝细听的姿态,与⾥尔克《杜伊诺哀歌》中“倘若我呼喊,谁在天使的序列中听见我?”的终极追问形成奇妙的共振:是否整个宇宙都充盈着呼唤?风声、⾬声、树叶摩擦声,莫⾮都是尚未破译的神的命名?
莫⾮
上帝也如此唤我们的名?
这⼀问,道出了⼈类最深的渴望:被铭记、被召唤、被确证存在。我们被命名,是因先被上帝认知(“我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赛43:1)⽽《创世记》2:19-20中,亚当为万物命名,代⾏上帝的创造权柄:“耶和华神⽤⼟所造成的野地各样⾛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前看他叫什么”。这⾸诗最终构建了多层命名体系:上帝命名⼈类,母亲命名孩⼦,⼈类命名世界。每个名字都是回声壁上的声纹,在呼唤与被呼唤之间,个体⽣命与永恒秩序完成神圣对接。
扎扎纳⽤这⾸诗温柔地推翻了语⾔的⼯具性。“⾔即⾏”(speech-act),诗⼈强调”说”(saying)这⼀动作,⽽⾮名字本⾝。母亲呼唤⼦⼥名字的⾏为,使空洞的⾳节转化为具象存在的孩童。名字不再是符号,⽽是对整个世界的建造。
唯有在被呼唤时,我们才真正存在。
母亲呼唤孩⼦,⼈类呼唤上帝,风呼唤倾听的⽿朵——在这永恒的呼唤与应答之间,⽣命被编织成闪耀的⽹。最后诗⼈“转⾝倾听”的姿态,暗⽰命名永不完成,既是将世界锚定的实践,又是向神秘开放的仪式,意义在风中持续⽣成。
如果“语⾔是存在之家”(海德格尔),那么这⾸诗似乎在进⼀步说:爱是语⾔之家。它⽤⼀种柔软⽽强⼤的⽅式告诉我们:爱,就是⼀种持续不断的、带有创造性的命名,也是最崇⾼、最恒久的命名。我们每个⼈的存在,都因被爱我们的⼈深情呼唤⽽变得清晰、完整⽽神圣。
我的⼥⼉叫Eliana,意为“太阳”,它还有⼀个含义是“神回答”。因为当我获知她的存在时,我感到我曾有过的困惑、犹疑和迷茫,似乎都在瞬间被解答,被清洗⼀空。⾄今,我依然记得那种爽朗、清晰和明亮感。
亲爱的读者朋友,你的名字是什么?在你的⽣命中,什么⼈会如诗⼈呼唤⼥⼉那般,远⽆⽌境、毫不羞怯、⼀遍又⼀遍地,唤出你的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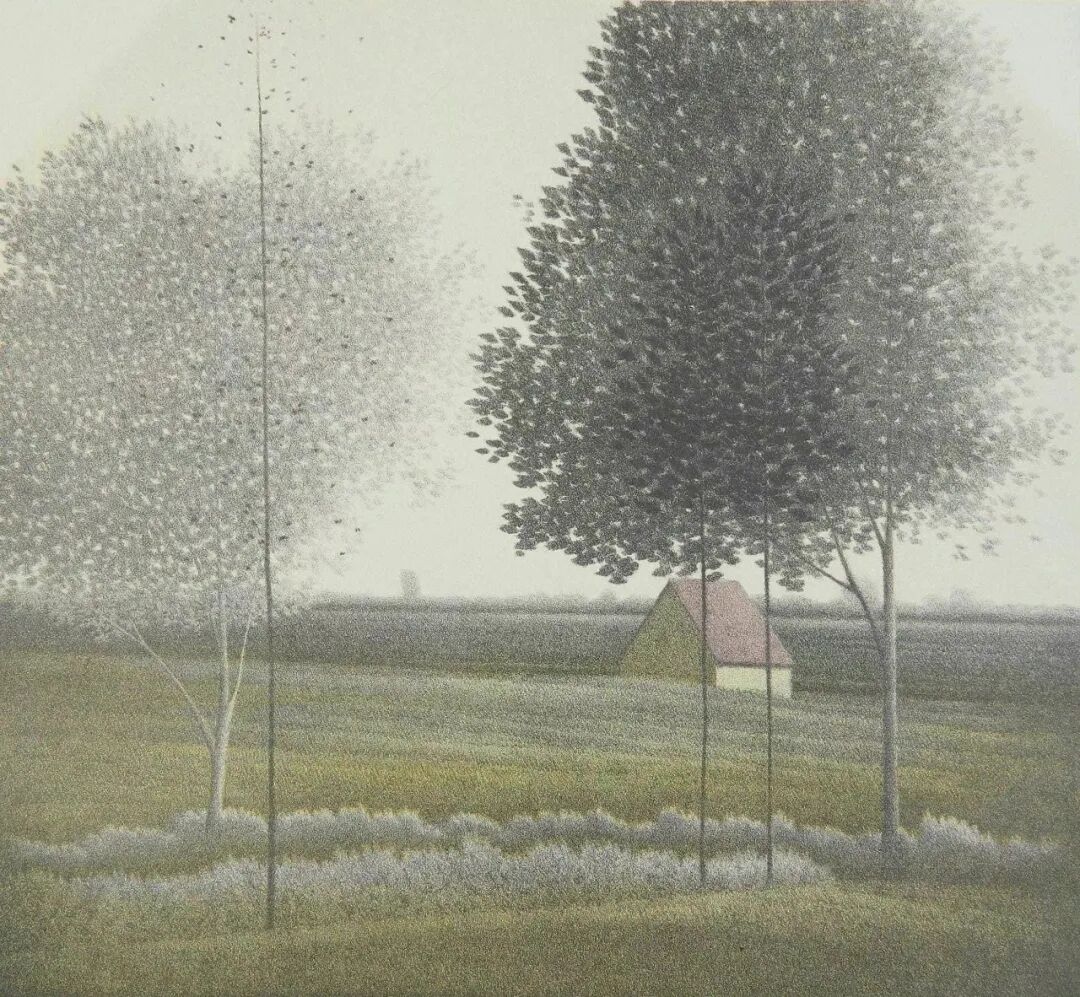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