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与说明
投稿信箱 / bedtimepoem@qq.com
微信号/ dushoushizaishuijiao
总编 / 流马
轮值主编 / 光诸 流马 金楠 冬至 曲木南 楚歌 唐晓丽 老汉
版面值守 / 小排 秋如线 黄璐逸 张看看 小鳜鱼 雪菲 菡纸 Scarrie 肖蕊 卡比丘
声优值守 / 五重 祭祀 张大顺 彭艳戎 格雷斯 小贝 小米 秋的童话 罗小早 雨衣 韬略
声优接引人 / 无语僧
运营 / 范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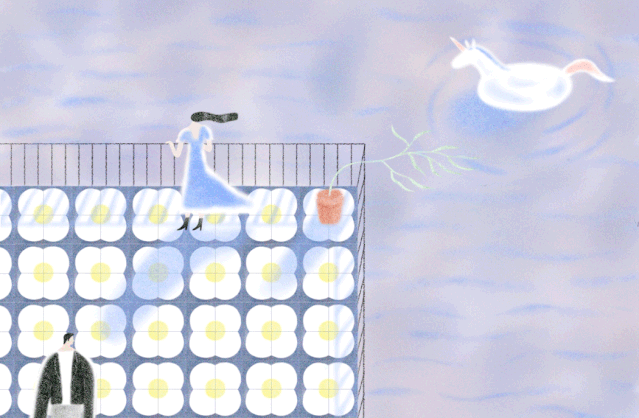
坐在烤焦的沙漠边缘的
酒吧里喝着劣等的威士忌,
那儿风从来就没有停过
沙从来就没有停过
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的汗
也从没停过,他不知道
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干什么
他既听不懂她说的话
又不熟悉她的身体,
就像他看不懂他自己。
他不记得在哪里
认识了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跟她
混在一起。他一直在瞅着
两只秃鹰为了一个死耗子
打了起来。他跟那个胖男人
酒吧的店主打赌说
只有一条腿的那一只会赢
他只剩下最后这点儿钱了。
他明白,要是他输了她肯定会
甩了他,但不知道要是他赢了
他又会拿她怎么办。
这两首诗在主题层面上,分别从男女的视角出发,目击并描写了同一段关系的覆灭,两者交叉阐释并互相抵牾,构成了一种虎符般的精巧对称结构,用可见文本的断裂、空白说出了文字本身未曾提及、无法说清之事;同时也是因为,这两首和之前推荐过的陆闵那首《运气之事》又构成了一种奇妙对称:两者都在讲述一段关系的毁灭,以及男女之间的无法逾越的永恒鸿沟。
而谈及毁灭,雷恩显然要更老辣一些。毁灭是雷恩诗歌写作的原点和母题——从个体生命到族群命运的毁灭,从毁灭者到被毁灭者视角的观察玩味——他可太擅长这个了。
男性视角这首以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开篇:
坐在烤焦的沙漠边缘
的酒吧里喝着劣等的威士忌,
那儿风从来就没有停过
沙从来就没有停过
顺着他的手臂流下来的汗
也从没停过,他不知道
他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干什么
他既听不懂她说的话
又不熟悉他的身体,
就像他看不懂他自己。
一言以蔽之,男人完全迷失在一种巨大而荒谬的生命处境里,其中一切方面都令他无法理解,他因此也无法理解自己。
此刻,这个男人能够确认的,只有自身的存在,以及依附其上、岌岌可危的生存处境(他只剩下最后这点儿钱了),和由这种生存处境支撑起来的一段可疑关系(他明白,要是他输了她肯定会/甩了他,但不知道要是他赢了/他又会拿她怎么办)。
他不了解何以置身此处,也不清楚和这个女人如何以及为何开始,两人之间甚至语言不通——简言之,万事万物其来有自,而他对一切一无所知。这是不是和陆闵笔下男性叙述者的不明所以而且不求甚解遥相呼应?
但是,他倒是能确认另外一件事:
他明白,要是他输了她肯定会
甩了他......
但是显然,这里的“他明白”,并非对客观真实的认知,而是一种“主观之内的所谓‘真实’”,也即偏见,这是一种存疑的“明白”;而更加荒诞的事,尽管他“明白”此事,但还是为事情的走向,安排了一种越发荒诞的决定方式:
两只秃鹰为了一个死耗子
打了起来,他跟那个胖男人
酒吧的店主打赌说
只有一条腿的那个一只会赢
自荒诞始,以荒诞为推进动力,在茫茫迷雾中间,依靠某种不可靠的主观认知驱动滑行,最后悬停在一种不确定性深渊的上方,戛然而止。
这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和男性思维:他们总是不耐烦透彻真实地读懂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不喜欢但能接受不知其所由的荒诞性;不喜欢且不能接受事情走向上的不确定性。
确定性,是男人心智里这一切荒诞的可能出口。为此,他不惜升级荒谬,借道随机,诉诸求死/自毁本能,来达成确定性的实现。
从现象上看,分手尚未发生,但男人已经,并将继续(如果不能奏效的话)作出选择,直至毁灭达成。那么,这这种选择是因,还是果?
我得说,这就是最低限度的诗歌。然后我又读到了这首《那个女人》。所以前面一首只算半首,评价要在完成后发生。
坐在烤焦的沙漠边缘的
酒吧里一张红色高脚凳上
那里的表土、沙尘
还有男人一直在变动不停歇
像停留在她脑海中的过往岁月
她看着这个带着陌生感的男人
在瞅着两只秃鹰争抢一个
死耗子。他的皮肤可真白啊
可身上原先的那股子硬气
却像蜡烛上的蜡油淌完了。
这不是她要的那个他。
这个长小节上来就声明了与前作场景的一致性和视角的对称性。然后,我们注意到,在同一事件中,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在心理姿态上的微妙区别:男人一直在呈现并向内感知自己,而女人把自己隐藏起来,坐在一张具有象征意义的红色高脚凳上,向外观察并且评价男人,将其置于比较的滔滔洪流之中:
那里的表土、沙尘
还有男人一直在变动不停歇
像停留在她脑海中的过往岁月
在这个视角下,她轻轻道出了简单到残酷、然而男人不知道的,关于两人何以一起的肇因:
他的皮肤可真白啊
以及这段关系行将崩塌的理由:
可是身上原先的那股子硬气
却像蜡烛上蜡油滴淌完了。
这不是她要的那个他。
很显然,前面男人诉诸随机的自毁选择是一种伪因,在这一系列荒诞行为的背后,是对真实因的模糊感应。
冥冥之中,两条命运之线相交在这座沙漠边缘的酒吧,凝结为一段共有的关系,并被悬置在同一个尚未发生的决定性现实之上(秃鹰争抢死耗子)。交叉的锚点由女人给出定义(男人很白);同时,她在此刻也已经决定好了相交之后重新分叉的理由(“硬气“的耗散)。
于男人而言,分叉将在赌局输掉之后发生;而在女人这里,分叉在主观上已经发生,只是等待男人给出形式上的确认,即来自赌局的结果反馈。
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三岔口式的处境里,存在两处令人意外的一致性:
一、他们都在乎这段关系,并将其理解为真正关键的客观实在,两首诗实际上是对这一重要资产的处置过程;
二、在对关系结束方式的描述上,他/她们不约而同地使用了“被甩”一词,即将动作的发起者确认为对方,而将自己定义为被动方或受害者。
这是另一处很有意思的断裂之处——哪个版本更接近真相?
为了支持各自的被动体位,他/她们对于接下来不可避免的关系毁灭也给出了自己的阐释:
对于男人而言,是“他只剩下最后这点儿钱了/要是他输了她肯定会甩了他”;对于女人而言则是“他肯定会甩了她/不是因为那赌金”。
这是一种奇妙的的二次递进:在南辕北辙的各自阐释中,钱不约而同地成为两者表述的共同焦点,只不过在男性这一侧,没钱被确认为原因;而女性这一侧,则特别否认了是因为钱。
冲突再次升级。
对此,男人以直觉感受到钱在一段关系里发挥的关键作用,但在主观上拒绝面对这一事实,于是逃往荒诞;女人接受,但拒绝承认这一点,可能因为这会把自己贬低到一种道义上的糟糕位置。
如果决定性因素不是钱,那又是什么呢?她在这里用另一个词置换掉了那个不能提及的钱字:
可是身上原先的那股子硬气
却像蜡烛上蜡油滴淌完了。
这不是她要的那个他。
硬气,是钱的果。不是因为赌金,但每次失败都是硬气的流失,她在意的是硬气,而这庶几算是一种普世认可的评价标准,一种值得坚持的站位。
显然,尽管看起来存在分歧,但“甩”这个动词的主语和宾语是确定的。是女人再次失望地甩掉了自己生命里的又一个可悲的失败者。
作为发起者、操控者,以及掌握更多信息的一方,在男人视角停下的地方,女性视角继续向前推进,结果终于发生,男人迎来了自己的崩溃:
当只有一条腿的那只鹰
败落时,他大笑起来。
赌局终结,男人输掉最后的筹码,两人的关系再无转机。矛盾冲突在此刻达成高潮并得以释放。男人的求死/毁灭本能实现,对此他报以释然,同时也是掩饰性的歇斯底里大笑;而女人呢?面对姗姗来迟的“被甩”,她立刻确认了“被甩”这件事,同时又心怀怨恨地咒骂并抱怨道:
龟孙子
他在微笑。上帝啊,她说,上帝。
他甚至都听不懂我说的话
不知道我说了什么,
还有我忍着没说的,和并非真心的话
尽管是冷静的决断者,但选择的失败(而非分手)仍然是难以忍受的,即使此类事件曾经反复发生。她还得为这种失望和怨恨找到一个正当的角度和理由,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对方,将注意力集中在男人的态度上(缺少赤诚的情感投入,以及沟通的失败),否则就必须在糟糕的状态下面对那个被小心翼翼隐藏起来的真实的自己。
所以你看,我们再次找到了之前从陆闵的《运气之事》里已经被揭示的结论:
女性是心思缜密的事实操控者,和现象上的被动者,男性则一贯地不明所以而且不求甚解,懵懂无辜但也十足可恨。
同样的事物,在两性视角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它们必须被小心翼翼地转译为不同的阐释文本,来达成内心的自洽。这些文本是真相的妆容,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文过饰非功用。
——当然,以上都是我们从文本中解出的东西。
然后再想想这个事实:诗人帕特里克·雷恩是个男的,所以,这样的对照和表述,所表达的,是男性视角下的观察和反思。既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叙述者,所以这当然也可能是男人们的阴谋:他所谓的无知懵懂并不可信——难道在懵懂背后,他们所贪图的,不就是肉体和情感上的片刻欢愉吗?这跟追逐金钱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而他们甚至拒绝掩饰这一点,只是将计就计地躺在猎物中弹的位置上,就足以占领道义上的正当性。
在每段关系里,残酷又细致的斟酌算计都是诚然存在、无法回避但又不可言说的。这种自怨自艾、欲罢不能、欲言又止和量变之后的突然一击,正是人类和他们的文化本身呀。
可能,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阳光坦荡的厮守理由,已经被主流话语言说的也未必正当。本质上,我们都是一群自私自利、言不由衷,可恨又可怜的人。也许拦在他/她们之间的,并非种族、语系原因的语言不通,上帝毁掉巴别塔,所变乱的并不是种族间的语言差异,而是男女之间,基于站位,在逻辑和语汇上的沟通的可能性。又或者,这种变乱甚至无关性别,它就是利益的不可调和性本身。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