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下雨,但我要去见你
因为昨天我没有去
明天也不会去
而后天,无论天气如何
我会再次去见你
因为大后天我不会去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这几乎成了我的一种习惯
是的,在我的习惯里
应该还包括这些:
去见你的那天我会想着
第二天不用去见你了
而不用去见你的那天我会想着
第二天将要去见你
作者 / 林东林
选自 / 《三餐四季》,文化艺术出版社
昨天北京下了一夜雨,当时我在编辑昨天的推送,没有听到。微信群里有人说下雨了,我才走到窗前,听了一会儿雨声。秋天的雨和别的季节不同,不论是听上去,还是实际上,都给人无边无际的感觉。以前人们形容秋雨,爱用“绵绵”二字,就是连绵不绝的意思了。于是北京以南的朋友说,明天秋雨就该下到我们这里了。
所以要问的是:今夜,你那里下雨了吗?下雨的时候,有没有打乱你原本要去见一个人的计划。尽管是下雨吧,因为要去见的是那个人,所以并不能因为一场雨而改变计划。因为这本来就不是计划,而是一种习惯。就算你没有想要见的人,根据习惯,此刻要下楼去走一走,那也不会因为一场秋雨而停止。
爱,大约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种习惯。这首诗准确地捕捉到了这种“爱的习惯”,但这是多么容易被忽略的“习惯”啊,尽管你有,但你常常觉知不到。而只有当你觉知到时,你对这场习惯之爱,就有了全新的认识。
在阅读这本诗集时,我常常觉得,诗人经常抽离自身,把时间中的日常当成一种静物去观察,揣摩,以一种冷静但不冷酷的眼光去勾勒,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去除生活杂质的透明、清澈、结晶的诗意,一种温凉的气质。我把他这种对日常重构的手法称之为“冷萃”。有意思的是,当我拿到这篇访谈,看到他说自己的诗歌更像“一粒明矾”,将日常生活澄清出来。虽然我们体认到的“工艺”不同,但好像有一点异曲同工。
据说今夜很多人又在磨刀霍霍准备剁手了,剁手之余,想想这三餐四季般流转的人生吧,也许对自己下刀时,会温柔些吧。
Q&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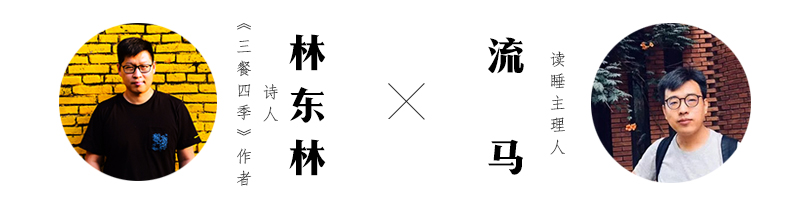
林东林:这本诗集有过三个名字,最早叫《一个普通的早晨》,后来叫《我的悲伤也有一部分属于你》。这三个名字,显示了我纠结的心路历程,这个纠结主要是对于市场的纠结——其实是枉然,一本诗集能有什么市场呢?最后叫《三餐四季》,是因为这个名字简单,不矫情。我这些诗歌中所写的主要也就是三餐和四季之中的这些日常生活;这个名字也非常契合我对诗歌的理解,诗在日常,写诗也是我的一种日常。
流马:你的确更在意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微观察、摹写。在一首叫做《此时此刻》的诗里,一个词很形象:摸摸弄弄。人们在无聊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这里摸摸,那里弄弄,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喝水或者不喝水。但实际上这种时刻往往是被人们忽略的时刻,就是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而作为诗人,是不是就是要将这种时刻觉知出来,让这种日常通过这样一种摹画,重新认识自己。你怎么认识诗歌与日常的关系?
林东林:确如你所言,《此时此刻》那首诗,我想写的也就是那种感觉不到自己存在的时刻、我们都曾经经历过的时刻。这种发现的功能,我想也就是诗歌和日常的关系,日常是我们庸常生活的本来面貌,但同时它也制造了我们的忽略、遮蔽和视而不见,而诗歌和日常的关系就在于,诗歌可以也应该成为日常中的一粒明矾,就像澄清一桶浑水一样,它可以澄清我们置身其中却往往又麻醉其中的日常生活,让一切都突然清晰起来。
流马:你正式开始写诗的时间并不长久,是回到武汉生活之后才开始?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让你觉得要写诗?
林东林:真正开始写诗,要从来到武汉的第二年算起。决定性的因素也不好说,它其实是合力作用的结果,一是我想从此前十几年的文化写作和传统写作——主要是散文随笔、评论和访谈——中挣脱出来;二是我想从之前多年的出版策划中跳脱出来,成为一个内容的创造者而不是包装者;同时,我在武汉乃至更大的范围内也进入了一个朋友都是诗人的圈子,所以我也就写了诗,这是瞌睡的人正好遇到了床。诗歌写作让我找到另外一种表达,一种更接近于语言而不是内容的表达,我觉得我也可以表达得很不错,相信我会一直持续下去。
流马:有没有一个比较隐秘的学习谱系,或者说,受哪些诗人或流派影响比较大?
林东林:笼统说,我受“第三代”诗歌的影响比较大,主要是韩东和杨黎,他们对我的影响并不在于具体的诗歌技艺,更多是一种气息和观念,是对待诗歌的态度。除了他们之外我也喜欢很多人的诗,也不免会受到他们的影响,米沃什,希尼,卡佛,布考斯基,布劳提根,这个名单可以开很长,它们也都对我产生了一些我并不能轻易指出的影响,这些影响内化到我的观念和文字之中,逐渐发展出了一些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源头在哪儿其实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我愿意接受这些影响,“愿意接受”这个主观选择我觉得比较重要,它是一个诗人在茫茫的诗歌版图中努力与自己气息相近的诗人靠拢的过程,这决定了他的气质和品位。
流马:你说人要首先建立起一种对诗歌的基本认识,才能谈什么诗,什么不是诗,以及什么是好诗,什么是坏诗。这种诗歌的基本认识应该如何建立?
林东林:多读诗,多读好诗,多读当下诗人的好诗。当然,这其实也不简单,一个人说的好诗和另一个人说的好诗可能完全是两码事,即使两个对诗歌的认识大体相同的人也会对一首诗的评价呈现天壤之别的差异。很可能很多读者对诗歌——当下诗歌——的认识基本上等于零,他们的诗歌经验更多地来自于古诗,来自于课本上的某些时期的新诗,来自于舒婷、海子或者北岛等等,来自于对诗歌的——社会集体观念赋予他们形成的——某种浪漫化和所谓的有诗意的想象,要纠正这种与时代完全脱节的诗歌观念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纠正的方式,就是要多读一些当下好的诗歌作品,多读一些西方自从惠特曼之后的诗歌作品,少读一些中国当代所谓名家和已经被经典化的诗人的诗歌作品,这样我想可能会建立起对他们对真正的诗歌的认识。
流马:你引用一位名叫卢辉的诗人的作品《世界的甜不一定都是甘蔗的》来说明好诗的基本特征,但是并没有细说好诗的基本特征都有哪些,希望读者去体会。别人的体会有时候也会和你的体会大异其趣。能否用最简要的方式谈谈你所认为的好诗的基本特征?
林东林:其一,简单、结实、每个人都能读得懂的语言;其二,不炫耀也不卖弄技术,不贩卖也不兜售不属于作者自己的东西;其三,能写出自己独特的发现和感受,见别人未见,发别人未发;其四,能够翻译成另外一种或者多种语言,且不损失掉它最核心的东西;其五,没有名句。就这么罗列下去的话,还可以罗列出来很多,不过也存在一个悖论,就是好诗是可以创造新标准的,它也许不满足于以上我所罗列的所有标准,但是并不妨碍它是一首好诗。所以,我也只能是印象式地给出一个通约性的看法而已,并不绝对。
流马:你说诗歌要“说人话”,又说“说人话”未必就是诗歌。那么,在“说人话”到“诗歌”之间,还有多少路要走?
林东林:说人话,意思就是不要说一些假话、空话、套话、怪话,不要说一些言不及义或者反反复复兜圈子的话,也不要说一些看起来很像诗但是其实不是诗的话,而是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平时说的话。“人话”的确是诗歌的第一步,尤其是好的诗歌的第一步,这个方向是对的。至于“人话”说到什么地步才能成为诗歌,这很难回答,因为这几乎就相当于要给诗歌下一个定义,但事实上诗歌恰恰是没有办法去定义的。但我想“人话”和“诗歌”的最大不同,就是“人话”更多是功能性的,它凭借它所言说的内容而得以成立;而“诗歌”却是非功能性的,它仅仅凭借言说本身——语言、语言之间的气息和节奏——就可以成立,而不必靠它所说言说的内容。
流马:相对于“言情”和“言志”的传统,你认为诗歌本质上是一种“言我”,能否谈谈这个“言我”。言我与前面两者的区别又是什么?
林东林:“言情”里没有“言我”么?“言志”里没有“言我”么?当然有,我的意思是说,相比于“情”和“志”之中那些集体化和社会化的东西,“言我”才更接近于个体感受,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公共化和集体化,它们才更加真实、鲜活和饱满,它们才离我们的肉体经验更近。这个“言我”并不是要我们在诗歌中只写自己的日常,而是要不断地去接近和发现在“我”身上具有的同时也是你身上和他身上都具有的那些部分,以“我”去补充我们。
流马:这几年武汉乃至湖北的诗歌群体发展非常亮眼,不仅有余秀华这样异军突起的优秀诗人,还有像张执浩、小引、黄沙子等让人印象深刻的诗歌中坚,他们的诗歌都曾在读睡不止一次出现过。能否谈谈武汉的诗歌生活和朋友?
林东林:我在武汉的诗歌生活,一部分是这些年来参与策划的各类诗歌活动,另一部分,是比较小范围的聚会,张执浩,小引,张羞,槐树,艾先,川上等等,大家一起聚聚聊聊。与其说这会带来一些诗歌观念的变化,倒不如说它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了自己的边界——他是那样的,他是那样的,而我是这样的——这是逐渐让你成为你自己的一种诗歌环境。余秀华,当然,她是我的所谓的“闺蜜”,我认可她的一部分写作,现在是不认同要大于认同,这种不认同并不是说我有多高明,而我是觉得她应该回到真正的写作上来,而不能永远顶着一个网红的帽子。
流马:武汉这个城市对你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林东林:我来到武汉五年了,尽管我一直生活在这里,但就我的写作来说,其实与这个城市鲜少发生关系,它可能会跟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地方的人发生关系。武汉这个城市对我更多表现在它是我的一种现场。它的物理空间、自然风景和人际关系等等为我提供了真实生活的血肉和肌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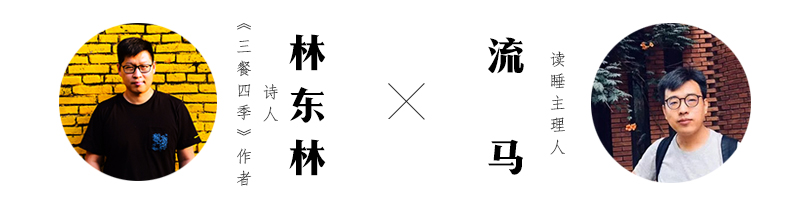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