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称
那时她还是个婴孩——
伊莱扎·莉莉。很快成了莉莉。
后来她是⾯包店的“斯图尔德⼩姐”
再后来是“我亲爱的”、“我的⼼肝”,“妈妈”。
三⼗守寡,她重回职场
成了“汉德太太”。⼥⼉长⼤,
结婚⽣⼦。
现在她是“奶奶”。“⼤伙⼉
都叫我奶奶,”她对客⼈说。
于是他们都这么叫她——朋友、商贩、医⽣。
在⽼年病房⾥
护⼠们直呼病⼈的教名
“莉莉,”我们说,“或者奶奶,”
但那不在她的档案⾥。
在最后糊涂的⼏周
她又变回了伊莱扎。
Names
When she was a baby -
Eliza Lily. Soon it changed to Lil.
Later she was Miss Steward in the baker's shop
And then 'my love', 'my darling', Mother.
Widowed at thirty, she went back to work
As Mrs Hand. Her daughter grew up,
Married and gave birth.
Now she was Nanna. 'Everybody
Calls me Nanna, she would say to visitors.
And so they did - friends, tradesmen, the doctor.
In the geriatric ward
They used the patients' Christian names
'Lil,' we said, 'or Nanna,'
But it wasn't in her file
And for those last bewildered weeks
She was Eliza once again.
这是⼀⾸⽤名字来叙事的诗。诗⼈表⾯在写⼀个⼥⼈不断变换的名称,实际是在写她的⽆名。
读到第三遍时,我感到这⾸诗的每⼀换⾏、每⼀称呼的转换,都是⼥性本质性存在与处境性存在之间的⼀次撕裂,⼥性的本体与功能的⼀次撕裂。从这些裂⼜⾥,我们可以看到,⼀个⼥性的⼀⽣是如何被规训的。
婴⼉时期,从“伊莱扎”(Eliza)到“莉莉”(Lil),她的名字被迅速简化(昵称化),⼥性⾝份已被家庭温柔地规约。
社会继续通过命名(naming)赋予她价值,“我亲爱的”、“我的⼼肝”已变成客体化、情感化的称呼,因为发出的主体是“我”,⼀个男⼈。
⽽她最漫长的⾝份——从“妈妈”到“奶奶”,则是将制度化的劳动,亲情化在家庭内部。她始终在家庭中承担繁衍和照料的功能,但她的付出并未留下个体痕迹。
当年,她的职业名(“斯图尔德⼩姐”)也⼀样,很快被婚姻掩盖,“汉德太太”的叫法虽出现在重新⼯作的场合,却依然保留了亡夫的姓⽒,似乎那个已不在场的男⼈,依然控制着她,对她宣誓着主权。
在⽣命的最后阶段,她隐⼊了⽼年⼥性这⼀“不可见”的边缘群体。她的名字在医疗档案中被忽略了,这是社会对⽼年⼥性贡献的系统性忽视。
这种冷漠的根源在于:当社会不再需要她扮演某种⾓⾊时,她的⾝份也随之⽡解。我们看到,她⼀直是某⼀个⼈的什么,⼀直是⼀种从属。⼀⽣中绝⼤部分时间⾥,她是⽆名的。
这⾸诗乍读并不让⼈错愕,甚⾄被⼀层朦胧的现实幸福所覆盖。我们知道,很多⼥⼈都是如此度过⼀⽣的,我们的奶奶、外婆,甚⾄母亲,她们的⽣活似乎也是充实的。
诗⼈的语⽓很模糊,这样客观纪实的记录,给⼈⼀种安然于命运的接受感,我们感到⼥主⼈公看待⾃⼰的⽬光,并不是苦涩的、或抱怨的。
诗人⽤⼀种隐忍、省略的笔法,让读者仓促地不知如何去感受。也许这正是诗⼈使⽤的策略,她想让我们初读时的体验本⾝,成为⼀种酸楚的警⽰:她从来不是⾃⼰⼈⽣的中⼼词,然⽽她是认可这种状态的。
名称的交迭变换可能悄⽆声息,但⼀个⼈对⾃⼰被他⼈覆盖的接受,应该并⾮天然。那些响动和疼痛,都被掩藏在历史的规训之中。
英国诗⼈温迪·科普(Wendy Cope)擅长⽤幽默笔触探讨严肃主题。做了多年⼩学教师后,⾸部诗集《为⾦斯利·艾⽶斯煮可可》(“Making Cocoa forKingsley Amis”,1986)取得空前成功。评论家兼诗⼈A.M.贾斯特在《洛杉矶书评》中宣称:“若要寻找⼀位像科普这样才思敏捷、题材⼴泛且技艺超群的诗⼈,我们必须回溯到拜伦的时代。”
我想科普是想让我们忍不住去问:你到底是谁?去除掉这些“主⼈”、这些关系和前缀,你——“伊莱扎”,你是谁?“伊莱扎”只存在了⼏个星期——在她⼈⽣的开头和结尾,形成了⼀个闭环。⼥性的⼀⽣就这样被社会脚本限定:从⼥⼉到妻⼦、母亲、祖母,最终回归⽆名状态。
如同百年孤独,这种循环揭⽰了⼀种⼥性命运的不可逃脱性。名字的短暂回归也并⾮解放,⽽是社会对⼥性历史的抹除——她的⼀⽣被简化为⼀个起点,中间的所有努⼒与存在都被淡化了。
最让我难过的是,作为懵懂的新⽣⼉和昏迷的将死之⼈,“伊莱扎”对她毫⽆意义。她听不懂,即便别⼈这样称呼她,她也不会将这个称呼与⾃⼰进⾏关联。
然⽽,那是她真正属于她⾃⼰的时候。⼀切⾝份尚未成型,⼀切⾝份皆以脱去,她是她了,但她不认识⾃⼰。
“名字”到底是什么?⼀个⽣命降临时,⽗母怀着最⼤的爱意为她(他)命名。这个珍贵的本名,与那个独⼀的所指之间,到底有没有本质的关系,很难说清,但你到底该如何称呼⾃⼰,如何在他⼈贴赋的标签与个体认同的存在之间进⾏分辨,如何为⾃⼰的⽣命寻找⼀个坚定、独特的声⾳,在这些问题⾯前,是需要驻⾜停顿、反复思考的。
很巧的是,我恰好认识⼀个叫“伊莱扎”的⼩⼥孩⼉。去年刚搬到新的社区时,常听到对门那户⼈家的⽗母叫她们四岁的⼩⼥⼉:“Eliza——”,尾⾳悠扬,宠溺深情。她听见呼唤,便蹬着⼩脚踏车,从我家车道折返,骑进⾃家的车库,回到两个正在玩耍的姐姐⾝边。
正式见⾯时,我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她⼤声地,⼀字⼀顿地说:“E-l-i-z-a——Eliza!”她母亲骄傲地看着她,又对我说,这是“Elizabeth”的简称,意思是“God is satisfaction”(神就是满⾜)。我没有听到过他们⽤任何简称来叫她。
我相信、也祝愿这个“伊莱扎”的⼈⽣,⽤她的全部名称写成的诗,将会迥然不同。你也⼀样,我亲爱的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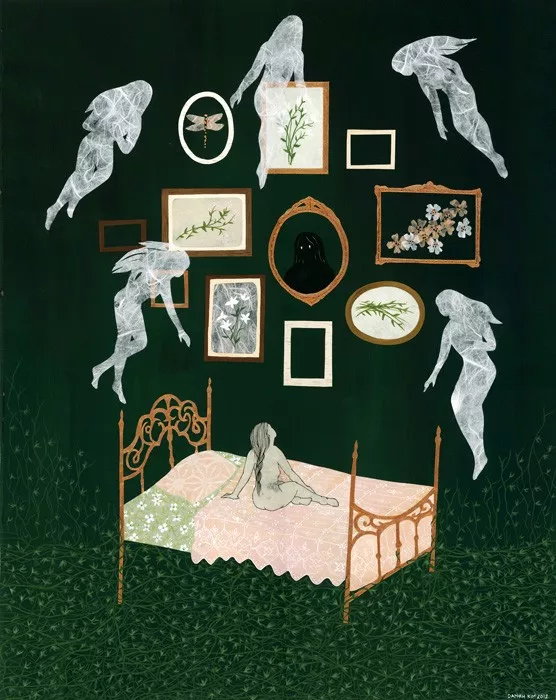

近期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