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与说明
投稿信箱 / bedtimepoem@qq.com
微信号/ dushoushizaishuijiao
总编 / 流马
轮值主编 / 光诸 流马 金楠 冬至 曲木南 楚歌 唐晓丽 老汉
版面值守 / 小排 秋如线 黄璐逸 张看看 小鳜鱼 雪菲 菡纸 Scarrie 肖蕊 卡比丘
声优值守 / 五重 祭祀 张大顺 彭艳戎 格雷斯 小贝 小米 秋的童话 罗小早 雨衣 韬略
声优接引人 / 无语僧
运营 / 范致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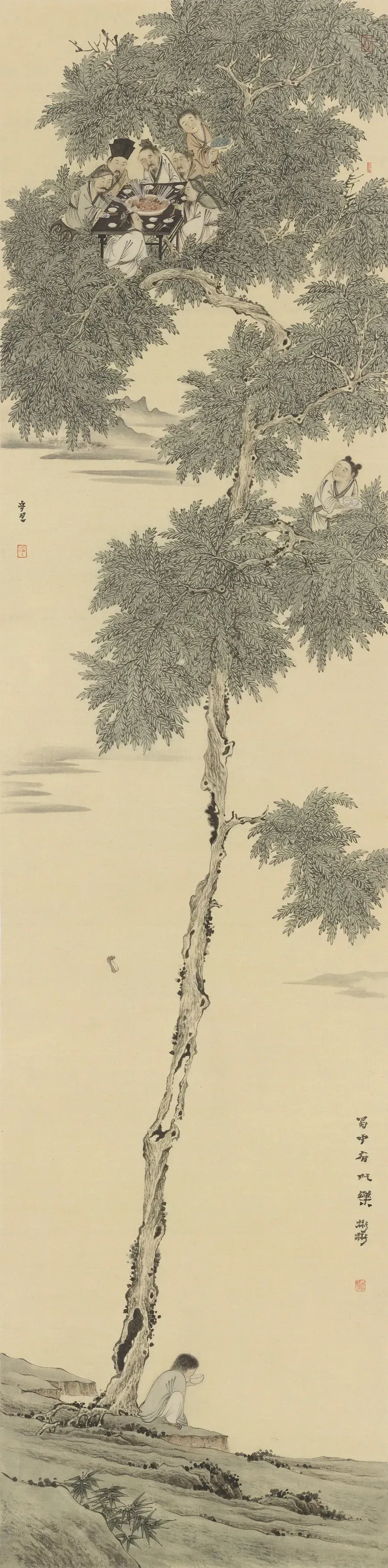
小雨游丝,在山城八月和草一样
我们没选择室内的座,这样
树和街对面店铺都要明澈几分
今天客栈的菜是烧金针菇牛柳、
豆角茄子、拍黄瓜和一壶苦荞茶
我试图问询啤酒,“还是算了”
起身结账前,抓起桌上那层杯底饮尽
在餐馆门口我们挥手就此别过
你衬衫的肩沾了风沙
也好,毕竟铁轨向西
你得携带些许 此地痕迹
语言既是日常交际的工具,也是层累至今的历史遗产。这就让所有写作者都面对如此局面:我们继承了一套丰富但老旧,可能已部分“失效”的语言工具,却必须用它来应对一个持续流变、某种意义上已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螺母和螺帽对不上,一旦这种失配暴露出来,我们就陷入表达与存在上的双重尴尬。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是千古名作,又因收入义务教育的语文教材,几乎成了全民记忆。安渡这首诗,题目作《送元二使安西 王维》,形式上是一次复写,却多出一层戏仿的腔调,我们几乎听得到人来疯的诗人要开始一段表演时的假模假式和洋洋得意。
安渡几乎逐句复诵王维的原诗,同时用当下日常的实况与情境去置换:渭城驿馆,成了山城街边苍蝇馆,而舞台深处的纷纷小雨保留下来,雨中的房屋街景也似乎不变。在这样的双重曝光之中,一些场景几乎丝丝入扣地重叠在一起,又有一些内容彼此逸出。一种暧昧而丰富的意蕴浮现出来,让读者忍不住去细细比对、辨认,在异同之间重新理解古今之变的奥义。
最有意思的是,安渡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转译成一场契诃夫式的戏剧场景:诗人在离愁别绪中,似乎想多要一件儿啤酒,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算了”。似乎出于社恐而拖延至宴席结束,又或者出于情感阈值的实际状况与喝个痛快之想象的不匹配。尴尬,这样一种异常现代的复杂情绪,从未被盛唐大诗人们写过。
“抓”住“那层杯底”的特写最精妙,仓促而狼狈、微醺而不知轻重,都在这一个“抓”字;说抓住的是“那层杯底”之酒,而不是杯子,则写出塑料杯之透明或纸杯之轻如无物。这正呼应着前文的“豆角茄子、拍黄瓜和一壶苦荞茶”,这些精确的镜头捕捉,充分调动了读者的感官记忆和日常经验,油腻腻的桌面、满地餐巾纸、嘈杂混乱的就餐环境,都自然地被逐一补全。
这正是每一个人嘈杂混乱的年轻时代所经验过的“离别”。我们都曾在语言和日常的不对位中,努力学习着(想象中的)一个成年人的情绪和情感,踉踉跄跄,跌跌撞撞。
大多数时候,人们其实没有足够的勇气智慧去面对语言和生活世界的不匹配,常常强迫生活世界去服从语言的秩序。对于创作者而言,那是不诚实的。使用总是有限、常常失效的语言工具,去面对持续涌现、不断变动的世界,去说出尚没有被说出的意思,这就是写作者的宿命。安渡这首诗,敏感、精妙地细描那种体用不匹配的怪异感,以一种“创造性误读”或“转化性嫁接”的诡计,去说出未被说出的尴尬而真切的体验。相对于当下某些对古典的恋物癖式的追摹潮流,这首诗无疑有力量多了。

近期评论